这个春节来得有点迟。腊月二十八九,殡葬热线服务电话 4008341834小区的杜鹃花就开了,长在墙角的红花酢浆草也在阳光下热烈开放,煞是美丽。
今年的春节之所以迟,原因是今年农历闰九月,多了一个月,全年有十三个月,导致正月延迟。但植物就不管那么多了,依然追随内心,如约绽放美丽。我家种的几盆春兰,平时默默无闻,临近春节的几天,纷纷抽枝,绿色的花朵节节开放。
植物最能感知春天的信息,它们听从春天的召唤。
一草一木,它们的内心都有一个春天。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故乡。

大年初二一早,我坐上一个老乡的车急急往500公里开外的家乡赶。
春节前,与朋友约好年初二回乡,看看亲人,会会老友,是一场轻松的回乡之旅。初一晚上,表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大姑走了。大姑九十一岁,对于她的离去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难过。我与表姐说,明天一早我就回来,争取能见大姑最后一面。如果路上不堵车,下午一点钟左右可以赶到。按他们那里风俗,二十四小时后是应该火化的。我和她商定,就等到下午三点吧。
大姑选择在年初一走,这个时间点对客家人有点尴尬。
客家人对春节极其重视,尤其是对年初一。初一是一年的“开门”,这天,客家人一般要选个时辰放爆竹,打开门,祈望新一年的吉祥顺利。吃完早餐,晚辈都要到同村的长辈家拜年,大家见面,互致祝福:“恭喜恭喜!过了新年身体健康,全家福禄!”
清康熙年间老乡林宝树著的通俗启蒙读物《一年使用杂字》在中国客家地区流传甚广,这本书的开头就是“年初一,早开门,放爆竹,喜气新”。这本书民间俗称为《年初一》,我小的时候也能背一点。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像我的家乡,福建省武平县这样的客家地区,在古时农耕社会,识字的人不多。林宝树,这位辞官回乡的举人,把客家传统风俗、婚嫁丧葬、红白喜事、季节农事等,用客家方言写成朗朗上口的韵文。全书共四千八百字,其中收进适合农村应用的单字近三千个,通俗易懂。
小的时候,我记得一位邻居的奶奶在大年三十去世。守孝在身,他们家的人是不能去别人家拜年的。大年初一,见人就讲“恭喜”,显然在他们家不适合说这个话。拜年的人都绕道而走,不敢进他们家门。最要命的是,办丧事的时候,很多平时关系不错的亲戚朋友,因为这年要办嫁女儿、娶媳妇等喜事,也不敢参加。亲朋之间,如果长辈去世都不来送一下,是很失礼的事,搞得几家多年没有来往。对于我来说,死者为大,更何况她是我九十一岁的大姑。如果能赶上,一定要见这最后一面。
大姑其实是独生女,关于家史,二十多年前我听母亲讲过一些,七八年前听大姑讲过一些,初步有一些轮廓。
我的家乡在福建省武平县的川坊村,与上杭县的寨背村交界。寨背村有一条大河,叫寨背溪,是汀江的一条支流。寨背溪的两岸,形成一个很大的集市,我们叫寨背圩。两县十几个村的人都赶赴这个圩市。早期是七天一圩,后来改成五天一圩。寨背圩是当地最重要的物流和信息流集散地,农民种的蔬菜、养的鸡鸭都挑到那里卖,远方亲戚之间的口信也在那里通过赶圩的人传送。小时候赴寨背圩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当年寨背圩的盛况至今还记忆犹新。听说现在已经式微了,而且凋零的不仅是圩市,寨背溪也成了一条小溪。
爷爷在寨背圩开了几间布店,当然是1949年前的事了。能在寨背圩开布店应该是当时的能人。我们几兄弟没见过爷爷,我母亲也没见过,因为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病死了。我只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大竹篓,里面装了许多花花绿绿的纸张,上面写着很古朴的毛笔字。后来经常和二哥聊起这件事,二哥知道那字是爷爷写的,他常感慨爷爷的字写得漂亮。没错,爷爷读过书,客家地区讲究耕读传家。临近寨背圩的地方有一座川坊村办的学校,叫培英小学,开办于民国初年,是武平县最早的学校之一。父亲也在那里读过书,小时候我玩的游戏,很多内容就有关于培英小学的。当然我没能在培英小学读书,我读书的时候已经叫川坊小学了。原来培英小学的地方已经成了水田,我还跟在生产队干农活的母亲去过,至今还记得那些历尽沧桑的老樟树和残缺的青砖墙脚。
爷爷只生了大姑一个女儿,客家人讲究子孙的传承,传承的责任在男丁。一个家族若没有男丁,就绝户了。有一年回乡扫墓,族人给了张我们这一脉的世谱。因为时间久远,也只能追溯到十二世。到我已经二十世,能传下来的支脉,都是有男丁之家。一个家族若没生到男丁,有钱的人就去买一个男孩,没钱有女儿的就采取招赘的办法。两条路都走不通,就只好任其绝户。爷爷向寨背村一个何姓人家买了我父亲,当时父亲只有一岁,大姑已经十六岁了。父亲几乎是奶奶和大姑同时带大的,所以父亲和大姑的感情极深。大姑嫁到上杭后,父亲还在上杭读了一段时间的书。
父亲的苦难是他们那一代客家人的普遍经历,不过他更可怜些。出生不久被亲生父母卖掉,青少年时代失去养父养母。他倔强地传承着养父的血脉,结婚生子,用木匠手艺养活家人。但他还是没有赶上好时代,无论如何努力,始终是一个苦命人。在四十八岁那一年撒手西去,一生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很多中国人记忆深处,都有一个温暖的姑姑。在中国的家族故事中,姑姑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她远嫁他乡,为夫家延续血脉,但她的心永远留在母家。她牵挂着家乡的父母,牵挂着兄弟,牵挂着兄弟的儿女,牵挂着家族血脉的延续。我见过不少兄弟之间反目为仇的,但很少听过远嫁的姐妹与兄弟反目的。在老家时,大姑来我们家是最开心的事,我们几兄弟出外读书,大姑在上杭县城的家始终是最温馨的一站。
在2002年的时候,母亲也离我们而去了。母亲自然是我亲情中最重要的一块,她的离去对我打击极大。在她离世后的几年我还经常梦到她,殡仪丧葬服务 4008341834在梦中惊醒。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虽然已割断了脐带,但精神的脐带,是多么难割断。
原本以为都年初二了,高速路上的车流会减少。但没想到还是车流滚滚,我们的车停停走走,我心急如焚。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我还是被堵在拥挤的亲情洪流中,赶到上杭,已近晚上七点。
我还是没见上大姑最后一面。对于中国人来说,七十岁后过世都属“喜丧”。大姑九十一岁的人生,算是圆满。去年她过九十岁生日时,我也专门赶回。这几年她的大脑已经萎缩了,记忆渐渐失去。宴席上,晚辈们都在逗她:“你知道我是谁吗?”白发苍苍的大姑咧开嘴笑,嘴中已无牙齿,一脸童真。我十分感慨,人生的轨迹原来是圆形的,九十岁的光阴,以为走了很远,却回到原点,回到童年。

年初三,我回到了川坊。母亲过世后,我就没有在春节的时候回过家乡,在川坊过年的记忆,已越来越模糊。后来回老家,一般会选择在春分时节。客家地区不少地方在春分时节扫墓。小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几兄弟去扫墓,父亲长年出远门做木匠活计,记忆中很少参加。读初中后我也没有扫过墓了,时间一久,我竟然记不得家乡扫墓的时间是春分还是清明。有一年恰逢清明节前,在闽西日报做记者的我在上杭采访,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聊扫墓的事,触发我心底里的乡情,我已好多年没回去扫墓了。清明节一早,我一人从上杭赶往相隔三十华里的家乡。那天恰逢寨背圩,人多路窄,车进不了村里,我从寨背村步行回家。刚走进川坊的村道不远,远远地看到母亲走来,她应该是去赴寨背圩的,发现我后,很惊喜地喊:“三腚,归来了。”我说在上杭出差,想顺便回来给父亲扫墓。她笑了:“你忘啦?我们是春分扫墓,我已经扫过了。”我才恍然大悟。
母亲死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奔走五百多公里,赶在春分这一天回去扫墓。尽管如此,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还是时常袭来。母亲走后,时间不断冲淡我对这个小山村的牵挂和情感。也许,对于游子来说,从回家里到回故乡的裂变,就在于父母。所谓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母亲走后,我们家的土房子也倒了,川坊也彻底成了我的故乡。
母亲的一生十分辛劳,她聪明、好强、倔强。从人情社会的角度,中国的农村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由于贫困,农民和农村的各种缺点都会显露和放大。父亲长年出门在外,母亲就要一个人面对世俗的纷争。虽然年幼,但我还是经常能感受到她的痛苦、无奈、寂寞。她几乎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干活,我想她应该是全村最早到水田里劳作的人。我家住在一个半山坳中,每天清晨母亲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小小的山路上,路上没有任何行人,只有寂寞的虫鸣声。每到傍晚,母亲也是踏着夜色回家。小时候,我也有过天黑后一个人从田间回家的经历,那种路无一人的害怕,经过一座座坟墓时的惊悚,记忆犹深。我至今也不知道,支撑母亲小小身躯的是一种什么力量。母亲虽然没上过学,但口算又快又准,我亲眼见过我们家卖猪卖鸡鸭时,她比一堆男人算得还快。她还经常通过口述,让我们兄弟给父亲写信,报告家里情况。
与我一起回川坊村的还有从广州回来的朋友老汤。老汤是上杭人,但川坊是他们汤家的祖籍地。这涉及一段历史,我也没想到,这个自己十分熟悉的、偏居一隅的小山村,竟然埋藏了六七百年的故事。
川坊如果是这个村的学名,那它的乳名就是汤坊了。在我小的时候,从来都说自己是汤坊人,周边村的人都称我们为汤坊村。据汤氏的族谱和一些传说,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汤氏先祖汤益隆为躲避战乱,携曹氏所生五二郎、五三郎逃离石壁,迁居福建武平县武东乡汤坊。汤氏定居汤坊后,逐渐人丁兴盛。
后来一场劫难从天而降。据传说是有位将军率部出征南方,途经汤坊时,为其地形吸引,认为“此村乃卧虎藏龙之地!”。他让前卫鸣锣开道,步行进村,以示敬重。不料几位在骑楼上拧线的妇女听到鸣锣觉得惊奇,起身观看时把碗里的水打翻,淋在将军头上,将军觉得她们是故意羞辱他。加之迎面来的百姓,没有一人向他下跪,他勃然大怒,下令对汤坊进行大屠杀。在这场浩劫中,只有汤四十八郎幸免于难,传说是躲在池塘涵洞内。汤四十八郎后来逃至上杭湖洋寨背厚洋定居,这里也成为上杭、武平和粤东地区汤氏的发祥地。
从汤五郎到汤四十八郎,汤氏在汤坊已繁衍了四十三代,可见人丁兴旺。
而林姓是什么时候来到汤坊?按林氏族谱的说法,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林宗仁在南京治好了皇后(或是妃子)的病,朝廷封其为医学大国手、大理寺卿,并准许在汤坊开基,故川坊林姓把宗仁之祖父万满郎尊为开基祖。林姓在川坊已繁衍二十多代,约六百年。到我已经是川坊林氏的二十世。
中国人喜欢聚族而居,客家人居住在山区,山高路远,居住历史比较长的村,一般只有一种姓,多姓氏的村,要么是集镇所在地,要么是一马平川之地。川坊村近三千人,百分之九十是林姓,有一个小自然村为江姓,一户黄姓人家近代才迁入。像我现在居住的广东顺德,由于是珠三角平原地区,自古富饶,迁入的人多,一个村的姓氏就非常多。中国人讲究宗族,各个姓氏都要修祠堂,兴旺起来的宗脉也要修祠堂,这样每个村都有很多祠堂,所以广东有“顺德的祠堂,南海的庙”的说法。祠堂以姓氏为核心,姓氏又以男丁为核心。顺德是水乡,河道密布,每年端午节,当地人喜欢划龙舟。我的故乡是山区,没有龙舟,我一直琢磨顺德人喜欢划龙舟的原因。后来才了解到,主要还是为了显示氏族的兴旺。每到端午节,各村同姓氏的男丁划着龙舟,到处巡游。而龙舟比赛,更是为显示氏族男丁的威武。
十年前,我和老汤在一个广东老乡的活动上认识。当我说出家乡的名字时,他告诉了我有关汤氏族谱记载的故事。我十分惊讶,因为是第一次听说。有了这层“同乡”关系,我们来往比较密切,多次邀请他“回乡”看看。
我带老汤他们四处走走,离乡几十年,我对村里已很陌生,迎面碰到的面孔,大部分都不认识。以前清澈的小溪已经变得又小又窄,这条本是人工挖出来的灌溉河长年成为村民倒垃圾的地方,不少人家还把房子建在上面。无规划,乱搭建,是中国大多数农村的状况。中国的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看到倒垃圾的、乱搭建的,谁都不好意思阻止。法治的理念,契约的精神,总是难以进入中国的乡村。中国农村治理的落后,让许多中国人失去了乡愁。
行走在祖先的故土,老汤表情平静。这个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的山村,怎么能勾起他的情怀?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山村还是很漂亮的。十八九岁时,我还写过这样的一首诗:
山 村
两条相吻的人工河
写着大写的人字
几座错落的绿馒头
年年岁岁喂养着一群山里人
夏日,晨阳披纱
村头百年老杉
支起小村朦胧的风景
杉树下终年香火袅绕
留下一堆堆的故事
轻轻地翻找
哪一个是爷爷奶奶的
日落时分
山道弯弯
飘下一群客家女
从山谷挑回暮色
诗中写的是家乡情景,比较真实。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村里还保存很多青砖房子。当然,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带老汤他们去参观林默涵的故居。默涵公是武平县的名人,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武平有“文武双星”之说,武是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文就是默涵公了。默涵公走出这个山村后只回来过两次,1996年回来时,我在龙岩闽西宾馆见到他。那时候他因为之前生过一场病导致记忆功能衰退,刚刚见过面的人转瞬即忘,但他却记得寨背圩和培英小学。他女儿告诉我,虽然很少回乡,但他其实也时时刻刻挂念故乡,在他弥留之际还喊着妈妈。他写的《狮和龙》的文章里面描述旧时村里的过年风俗,我也感同身受。
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新年是怎样的热闹和有趣。除了有新衣穿,有好东西吃,大人们都一改平时的严厉,变得特别地和颜悦色之外,最使孩子们高兴的,是从年初三到元宵节这一段时间,几乎每天的白天都有耍狮子的,夜里有耍灯的,到我们乡间,向那些祠堂或比较有钱的人家拜年,表演。这不但孩子们爱看,也是乡间的人们一年仅有的娱乐。过了元宵,他们就又要忙起来了。
灯有马灯、龙灯和船灯。最受人欢迎的自然是船灯。这是用各种彩色的花纸扎成的旱船,上面装置了许多灯火,一个艄公在船头,一个少年扮的艄婆在船尾,一边摇船一边唱,还有一个叫作“十班”的乐队,吹箫拉琴的来配合。他们所唱的,自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名歌妙曲,但它朴素,诙谐,也间或带点对于世态的嘲讽,在乡下人听来就觉得是蛮有味道了。
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执导过一部名为《天堂电影院》的电影,讲述的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一个小孩多多与小镇“天堂乐园戏院”放映师的故事,因为电影,他们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感情,放映师引领他的成长,小多多的理想就是成为像艾费多那样的电影放映师,但放映师劝小多多离开小镇:“不要在这里待着,时间久了你会认为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走出小镇后,多多最终成为了一个大导演。
在中国,何尝不是这样,许多少年走出了小村庄、小城镇,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川坊村也是如此,默涵公如果不走出去,也许就和族中很多的公公叔伯一样默默终老一生,就像我未见过面的爷爷,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与默涵公同时期走出川坊的还有林伟,他参加过长征,是共和国的少将,他曾把长征时写的日记结集成书——《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村里读书的风气很盛,很多人从这个小山村考上大学。改革开放后,不少人去沿海发达地区创业,在福建厦门、广东东莞,一些人的生意已经做得非常大。据说,平时在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学校学生也越来越少,附近村的小学已经没法办了,学生都到我们村小学读书。中国城镇化的抽水机,把农村的人口不断抽到城镇。几年前,一位亲戚问我,要不要在武平县城买房?我回答是,赶紧买。他问为什么,我说武平是四十多万人建一个县城,房价肯定会涨的。
老汤他们走后,我去一位叔叔家吃饭。他承包了村里在“大路上”的一个山场,种了几十亩的橙子。我们踩着泥泞,走了约两公里的山路,去他在山场的家。走过的山坳,路过的水田,是如此熟悉,三十多年前,我不知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回。几个山塘还保持原样,那株百年老杉树依旧还在,只是一路上看到的水田都已经抛荒。
“大路上”临近五坊村,该村住的是吴姓和林姓人家。川坊村曾经有一段时间叫三坊村,后来因为本县的十方镇也有一个三坊村,所以改成川坊村。在广东江门市创业的格明是五坊村人,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回来,他说在五坊家中。叔叔知道他家,说他父亲早年是我们村小学的校长,我们转了一个山坳就到了他家。格明见到我十分惊喜,没想到大家在老家还可以见到面。吴总的公司去年在创业板上市了,他也成了这个小山村不多见的亿万富豪。他的房子原来在五坊比较偏远的地方,但他自己出资几十万修了一条水泥路到家门口,并在老房子前面盖了一栋新房子。他说,新房子盖好后,他也把老房子加固保留了下来,作为一种纪念。我想,这老房子一定保存着他很多记忆和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格明和我都在离这里五六公里远的丰田中学读初中,只不过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刚毕业。虽然我们在学校没能见上面,但丰田中学从他那一届到我这一届却创造了一个武平县农村中学的奇迹。丰田中学在丰田村一个叫竹山背的小山岗上,几排土夯的平房是教室和宿舍,周围种了很多高大的板栗树与油桐树。每到春天,油桐开着满树的花,一场雨后,满地是雪白的花瓣。板栗树也是在春天开花,气味浓烈的板栗花在校园飘散。秋天板栗成熟时,每个学生也可以分到一袋果实。在这个偏居一隅的山村中学,老师和学生吃住在一起。每天天蒙蒙亮,校长带着所有老师和学生一起跑步锻炼,早读的时候,老师已经来教室了;晚自习时,老师也在学生身边,真正是二十四小时在一起。学校周围都是农村、农田,大家确实也没有地方可去,就专心致志教书读书。那段时光,十分艰苦。我们每天吃的是家里带的咸菜,学校没有澡堂,所有的学生无论男女,都在丰田村的一条河里洗澡。学生每个学期都要交三百斤烧饭用的柴火,我那时个头小,都是母亲分几次走十几华里山路挑到学校。初中毕业后,我们很多学生都能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武平一中。后来,丰田中学也慢慢式微了,现在已改成丰田小学了,我们失去了初中的母校。
故乡变得陌生了,母校失去了,但也阻断不了奔向故乡的路,因为亲人和亲情还在家乡。春节对故乡的眷恋,就像绿叶对春天的思念,不需要提醒,总会在细雨中如约而至。
陈博士也从广州回到上杭的老家,陪伴他八十多岁的母亲。我到他家拜年时,他告诉我,春节回家的任务就是好好陪陪母亲。他陪母亲走亲戚,陪她散步,陪她聊天。在这个物资已很丰盛的年代,陪伴是给亲人最珍贵的礼物。在北京工作的老黄忙完公务赶回家乡已经是初二的凌晨三点,但他睡了几个小时就起来散步,迫不及待地呼吸家乡的味道。谢教授去年在出生的山村重盖了房子。年前他早早就回家乡,写春联,和父母一起杀鸡宰鸭,完全以传统客家人的方式迎接新年。
寻找乡愁,不忘初心。记住出发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回归传统中寻找精神的归属,寻找精神的信心和支点。
我在初五回到了顺德。出福建,下广东,一晃已经十七年。初六中午和几个朋友在六号花园吃饭,吃上几口铜盘蒸鸡、清蒸鱼,觉得是多么美味。看来,自己是真正融入了他乡。
下午,我在顺德新城的一个湿地公园散步。公园的树已经绿意葱葱,春天的阳光很柔和,公园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人在人工湖钓鱼,显得十分宁静和舒适。我似乎还没完全从故乡的春节气氛中缓过来,耳畔还回响着鞭炮声。放鞭炮是客家地区春节的“主旋律”。回乡期间,我和朋友去了一趟临近的清流县农村,路上所见,都是卖鞭炮的摊位,红彤彤的一排排,极为壮观。耳畔听到的,也是连绵不断的鞭炮声。朋友告诉我,当地人拜年,都带一挂鞭炮上门,先放鞭炮再进家门。整个春节下来,听到的都是鞭炮声。我在他家只待了半天,耳畔的鞭炮声却几天没有过去。
顺德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十几年前就禁了鞭炮。几年前,许多所谓民俗专家呼吁春节放鞭炮,增加“年味”,许多城市跟风解禁,但顺德不为所动。顺德的做法是对的,宁静的空间,清新的空气,比所谓的年味重要。
如果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强化“市场之手”的作用,在社会治理方面就应该强化“政府之手”的作用。当然,“政府之手”的作用更多要善于依靠改革,依靠法制来实现。民俗也好,社会风气也好,是需要政府来引导的。十几年前顺德推行的殡葬改革就很成功,记得刚刚来顺德时,每到清明节也是到处鞭炮声声,各个小山头还经常因为扫墓而起火。后来大家都去公墓拜祭了,那些乱坟岗也恢复了植被。殡葬改革在中国其他地方曾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在顺德能顺利推进?我想跟顺德的工业化发展有关,顺德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县区,不但机器进来了,工业文明也进来了。工业文明能推动地方移风易俗,接受现代生活方式。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全国两会,乡愁、乡村治理等农村话题自然受人关注。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应该激发与发扬“告老还乡,参与乡建”的传统,鼓励与支持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还乡”,以此改善农村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的落后面貌。中国在历史上有“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传统,由此形成了中国几千年的乡绅阶层。五百六十多年前,顺德的乡绅们借黄萧养农民起义的平定,向朝廷上书提议设立顺德县。同时期的佛山季华乡,一帮乡绅在佛山祖庙精心策划组织,抵住了顺德农民起义军黄萧养的进攻,保住一方平安。而我故乡武平县的乡绅林宝树,编写了通俗启蒙读物《一年使用杂字》(年初一),成功地在识字不多的广大客家农村地区推广了中原文化和礼仪,延续了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
但毕竟时代变化了,我们早已进入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社会,“互联网+X”改变了一切。在乡村,也许微信起的作用就能远远大于乡绅。很多远离故土的人在他乡生活的时间已经多于故乡,疏解乡愁的办法很多,有高速、高铁、飞机和互联网。不像我们的古人,乡关路远,只能对月思乡。我有几个好友去了加拿大和美国生活,但有了微信群,一帮朋友每天都可以交流,知道他们每天的生活与活动。
也许,故乡是用来回忆的,而不是用来回去的。
记得母亲在世的时候,面对生活的稍稍好转,面对困顿生活中的转机,经常说一句话:“想都想不到。”她在世的时代,改变是多么的难得,生活中出现一点惊喜足以让她心花怒放。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生活时刻在发生变化,我们时时可以想到。
(本文摘自《社会的体温》,林德荣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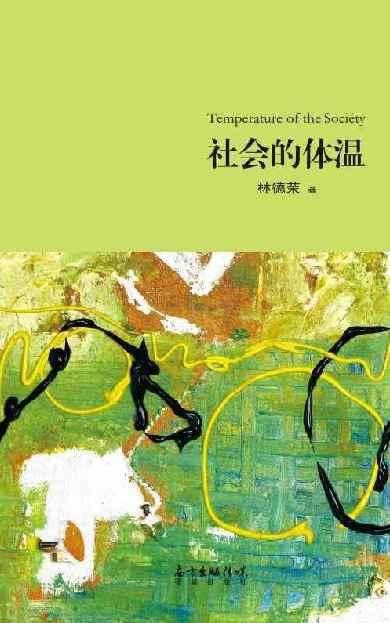
林德荣,1970年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从事过二十年新闻工作,新闻专业高级职称,是多家党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主撰者,作品八次获省级新闻奖一等奖。曾任广东省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已出版《可怕的顺德:一个县域的中国价值》(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中国千亿大镇》(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个人的篝火》(广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著作。